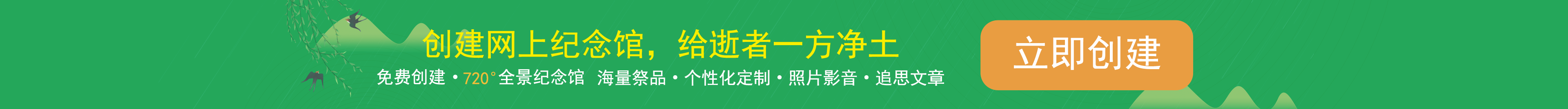填写逝者信息一
填写逝者信息一



 填写逝者信息二
填写逝者信息二
普通馆
免费
中级馆
{{jibiaLevel[1] ? jibiaLevel[1].price : '98'}}/年
高级馆
{{jibiaLevel[2] ? jibiaLevel[2].price : '198'}}/年
尊享馆
{{jibiaLevel[3] ? jibiaLevel[3].price : '398'}}/年

 逝者一
逝者一



 逝者二
逝者二



 创建完成
创建完成
 逝者信息
逝者信息



 绑定并登录
绑定并登录
普通馆
免费
中级馆
{{jibiaLevel[1] ? jibiaLevel[1].price : '98'}}/年
高级馆
{{jibiaLevel[2] ? jibiaLevel[2].price : '198'}}/年
尊享馆
{{jibiaLevel[3] ? jibiaLevel[3].price : '398'}}/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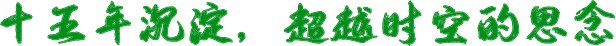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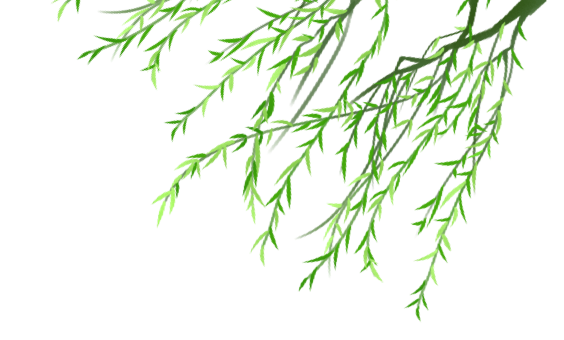






 邀请追思
邀请追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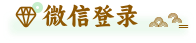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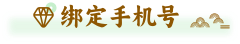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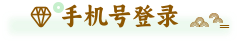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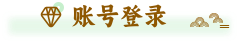




 同意
同意

 复制
复制